贺耀敏|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创新:一部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评《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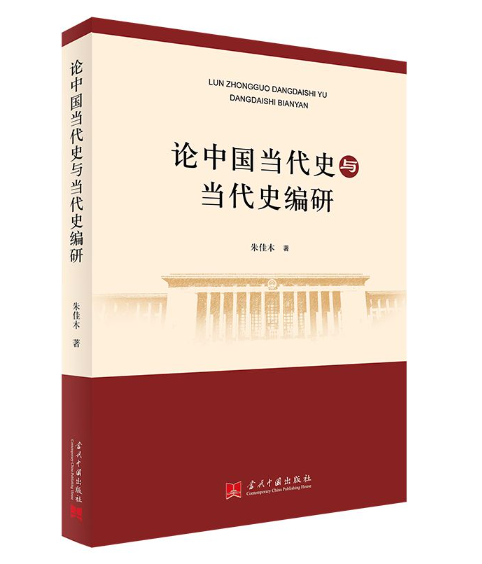
[关键词]理论与方法;国史研究;当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朱佳木长期参与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领域的科研规划制定与学术研究工作,在学术界理论界特别是国史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2024年初,他所著《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出版。这是一部汇集作者对国史编研长期理论思考成果和实践经验总结的重要著作,是一部国史研究具有基石性意义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围绕国史编研和国史学科建设展开,重点围绕什么是国史和国史研究,如何划分国史发展阶段,什么是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如何科学总结国史发展的基本经验、规律与特点等问题进行阐释,内涵丰富,认识深刻,见解独到,富有创新性,对于国史研究编纂和宣传教育工作具有较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一部理论与方法双重创新的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下面谈谈本书的一些创新与特点。
反复强调国史研究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五史”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学界取得了一大批重大成果。其中,新中国史研究领域繁荣发展的局面更是独占鳌头,这一切都与作者的长期努力和大声疾呼分不开。事实上,《论中国当代史与当代史编研》一书就是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五史”论述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学术展开。
作者十分注重和强调国史研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书中他分享了从事国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和方法论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对于国史研究者来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必须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指导思想的突出强调主要是基于国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肥沃土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指导思想。该书强调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重要文献精神,阐释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史,阐释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历史。
国史研究不仅具有史学研究的一般意义,还具有时代进步的特殊意义,不能仅仅用指导一般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来指导国史研究。作者毫不隐讳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观:“在不同历史观的支配下,对同一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解释。尤其在对国家史的解释上,更会有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从不同利益出发的交锋。”他在总结了国内外大量的历史事实后严肃地指出:“凡是要捍卫一个国家的独立、维护一个政权的统治,都必定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凡是要分裂、灭亡一个国家,推翻一个政权的统治,也总是要从对国家史的重新解释入手,以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在国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反复强调国史研究要始终坚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对于历史研究者包括国史研究者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五花八门的历史观点,能否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历史的主线,直接关系着能否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原因,认识其特点,掌握其规律,预测其趋势。作者明确提出国史“三条主线论”,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认为“在这三条主线中,第一条最重要,但它代替不了另外两条……迄今为止在国史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答案……它们就像三个主题,交汇演奏了和正在继续演奏着恢宏壮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交响曲。”他清晰地回答了历史的主线就“是指贯穿历史全部过程并始终支配历史沿着某种既定方向前进、反映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脉络”。正因为如此,他明确指出国史的主流是向好的,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
为什么要提出国史的主流问题,这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到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错误学术思潮的干扰与影响,一些人无法正确认识和判断改革开放前的那一段历史,无法科学理解和总结改革开放前的经验与教训。针对这种无法分清国史主流与支流、成就与失误的问题,他态度鲜明地表示要“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必须分清那段历史的主流和支流。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虽然有曲折,但它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主要的”。为此,他提出了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历史失误和错误的“四观点说”: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权衡轻重,分清主流与支流;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某些历史事件中有失误、错误就全盘否定那些事件;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他坚决抵制和严肃批驳那种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并从理论与史实上指出了历史虚无主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反复强调国史研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新中国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光荣奋斗史、中国社会主义的辉煌发展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史,新中国成立以来75年的历史进程是不容人为任意割断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做出了明确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作者很早就提出要正确看待和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相互关系。他认为,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即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割裂的、对立的,还是继承发展的、内在统一的,决定着对新中国历史的评价,也决定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他从“五个方面”分析论述了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对改革开放的影响: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环境。在论述改革开放时期与前一历史时期的关系时,从“五个超越”进行了系统分析: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超越;在政治体制上的超越;在经济体制上的超越;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超越;在国际战略上的超越。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统一整体性时,从“五个没有变”进行了系统分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变;坚持对外总方针总政策没有变。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关系的最为系统科学的论述,对于深入开展中国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架起了稳固的“跳台”、铺设了翱翔的“跑道”。他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后开创的,但它不是在新中国刚成立时面对的那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上开创的,而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并已进行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当代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反复强调国史研究要始终坚持将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任何学科要想最终作为一门科学而立足,都需要有自己合乎客观规律的,独立、完整、系统的学科理论”。作者为国史研究倾注大量心血,长期呼吁有关方面赋予国史研究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学科地位。他采取科学严肃的态度,综合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方法,力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论发展史、学术发展史、政策发展史等进行梳理,提升国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收入本书第一部分“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中的多篇论文,都是作者关于国史学科建设与学科理论创新、国史理论研究与国史研究长期思考和不断呼吁的见证。这是对国史研究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与归纳,是对国史学科建设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对于今后国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作者看来,“当代史理论研究除了有助于对历史作出更深刻更透彻的阐释外,还可以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解读时事、预测未来”。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论,为我们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事例,这一结论就是通过对世界史的理论研究,发现近百年来西方逐渐由盛而衰、影响力不断下降,东方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则逐渐由衰变盛、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规律而得出的。他大声疾呼:无论是国史学科“三大体系”的建设,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树立,都要求国史学科建设和国史理论研究队伍自身建设要加快发展。
反复强调国史研究要始终坚持将跨学科研究和专题研究结合起来
国史研究因其对象关联的广泛和发展的特殊性,需要我们从多个视角、多个领域、多种学科进行学术研究,既要有“纵”的长期发展和纵向联系方面的研究与剖析,又要有“横”的历史切面和横向联系的研究与剖析;既突出“条”的研究和分析,又考虑“块”的研究和分析,这就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在这部著作中,收录了《研究当代中国史离不开对世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中国当代史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当代史专史与通史在分期上的异同》《高度重视当代国外中国学的研究》等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文深入论述了国史研究中有关跨学科研究和专题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相互关系,为深化和拓展国史研究领域和视野提出了许多重要指导。
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更好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有两个方面的跨学科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另一方面,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我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存在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
反复强调国史研究要始终坚持大历史观
国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态度,这是需要国史研究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要坚持大历史观的问题,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这实际上就是对党史、国史研究的方向与导向提出的根本要求。
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一文,从国史研究角度,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也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验应当注意的几个方法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国史研究在总结经验方面的若干基本方法:既要研究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验,又要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联系起来研究;既要研究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历史经验,又要从宏观层面对历史经验作综合研究;既要研究国史中的成功经验,又要注意对失误和挫折的经验进行研究;既要用今天的眼光研究新中国的经验,又要把经验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既要研究本国的历史经验,又要把别国的经验与本国的经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等等。这对于深化国史研究、提高国史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在倡导和推动国史研究过程中,从不掩饰这一学科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与此同时这一学科还具有探索客观真理、反映客观规律、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遵循学术规范的基本特性。他认为:“史学研究一般分为史实研究和理论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它们为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史学理论研究更偏重于理论和解释工作,“要重点研究和揭示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规律、经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评价,并对修史本身的宗旨、原则、方法及历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进行研究”。“无论史学理论研究或历史解释,还是史实研究或历史叙事,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一定历史观的支配”。他的这种大历史观并不是放弃和否定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是要强调国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性。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那就是“史学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其中尤以对国家史的研究为甚。中国的当代史与古代史、近代史不同,是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生长的历史;与当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也不同,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不受私人资本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具有更加显著的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性”。事实上,在国史研究中,的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和问题,例如,一些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采取了全盘否定或大部否定的态度,这本身就背离了史学研究的根本原则。
难能可贵的是,这部著作还为我们提供了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处理党史、国史重大问题时采用的科学方法和政治智慧的经典案例,提供了胡乔木等分析和研究党史、国史重大问题时理论思考的经典案例,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和学术大家有关党史、国史研究的故事,读来让人无比神往、无限感慨。
总之,这部著作坚持唯物史观和国史编研的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注重学理性、应用性和前瞻性研究,既致力于国史研究自身的学科建设,研究探讨国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规律与特点,探索构建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又关切国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我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对于国史和党史的学习教育、研究编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定会极大地推动国史和党史研究工作,有助于促进国史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
[作者简介]贺耀敏,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